來源:www.chinancc.net 作(zuò)者:直面心理(lǐ) 發布時間:2021-04-14 10:37:16 字号: 大 中(zhōng) 小(xiǎo)
編者按:
近來,學(xué)生跳樓事件頻頻發生,孩子們處在疫情大環境中(zhōng),面對學(xué)習方面的壓力,家庭氛圍的影響,做出了這樣的選擇,着實讓人心痛。
本文(wén)《那份擱置的哀喪》描述了一個孩子自殺案例的心理(lǐ)分(fēn)析,以及孩子父親未能(néng)完成的悲傷。希望有(yǒu)更多(duō)的家長(cháng)看到本文(wén),因為(wèi)編者覺得這是避免悲劇再度發生的最好的文(wén)章。加一句,文(wén)章有(yǒu)點長(cháng),請耐心細緻的看層層深入肌理(lǐ)的心理(lǐ)分(fēn)析。

那份擱置的哀喪
文(wén) / 王學(xué)富
引子:
阿平18歲的女兒自殺身亡。接到噩耗,阿平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接着,他(tā)就被悲傷、憤怒、羞恥、自責的情緒淹沒了。他(tā)匆匆趕到學(xué)校,快速處理(lǐ)了此事,又(yòu)匆匆趕回家,草(cǎo)草(cǎo)安(ān)葬了女兒。這一切都是悄悄進行的,沒有(yǒu)喪葬的儀式,沒有(yǒu)通知任何親友,甚至,阿平都沒有(yǒu)把這件事情告訴自己的父母。
阿平是一家公(gōng)司的總經理(lǐ),他(tā)的公(gōng)司一直發展得很(hěn)好,但最近開始蕭條起來,生意每況愈下。20來年馳騁商(shāng)場,阿平經曆了多(duō)少坎坎坷坷,每次他(tā)都能(néng)憑着自己的能(néng)力讓公(gōng)司“起死回生”,但這次不同,看到自己苦心經營的公(gōng)司瀕臨倒閉,他(tā)竟無動于衷,不想做任何努力去做挽回。阿平之所以前來尋求心理(lǐ)咨詢,是因為(wèi)他(tā)想弄明白,到底什麽地方出了問題,是公(gōng)司,還是他(tā)自己?
面談進行了幾次之後,一個隐藏的事件浮現出來:就在一年以前,阿平18歲的女兒自殺身亡。當時她還是大二學(xué)生,因為(wèi)失戀,在一個夜晚,她從宿舍樓跳了下來。第二天早晨,人們看到,在陽光之下,她殘損的軀體(tǐ)像一棵被砍伐的樹,倒伏在人行道邊。
接到噩耗,阿平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接着,他(tā)就被悲傷、憤怒、羞恥、自責的情緒淹沒了。他(tā)匆匆趕到學(xué)校,快速處理(lǐ)了此事,又(yòu)匆匆趕回家,草(cǎo)草(cǎo)安(ān)葬了女兒。這一切都是悄悄進行的,沒有(yǒu)喪葬的儀式,沒有(yǒu)通知任何親友,甚至,阿平都沒有(yǒu)把這件事情告訴自己的父母。然後,阿平就趕回自己的公(gōng)司,重新(xīn)投身到生意中(zhōng)去。
喪失女兒之後,阿平和妻子平日都會避免談及他(tā)們的女兒,怕引起對方的傷心。但在他(tā)們的内心深處卻留着一個空位,即使後來他(tā)們領養了一個孩子,那個空位也沒有(yǒu)真正得到填補。阿平總是試圖說服自己:“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。”但是,他(tā)和妻子都意識到,女兒似乎從來都沒有(yǒu)離去。雖然他(tā)們日常生活中(zhōng)小(xiǎo)心翼翼地回避談及女兒,但夢中(zhōng)卻對女兒魂牽夢繞。雖然家中(zhōng)所有(yǒu)與女兒有(yǒu)關的物(wù)品都被搬走了,但女兒的言談身影還萦繞在他(tā)們的記憶裏,彌漫在周圍的空氣裏。

為(wèi)了忘卻,阿平拼命工(gōng)作(zuò)。一度,他(tā)以為(wèi)自己已經忘掉了。但過了一段時間,阿平身上開始有(yǒu)了一些變化:他(tā)時而會對溫柔體(tǐ)貼的妻子發火,時而會在辦(bàn)公(gōng)室當着員工(gōng)的面摔東西。事後,他(tā)又(yòu)為(wèi)自己的這些行為(wèi)後悔和自責。這樣的事多(duō)了,妻子跟他(tā)說話越來越少了,盡量避免觸碰到他(tā),公(gōng)司的員工(gōng)也開始回避他(tā),暗中(zhōng)有(yǒu)點人心惶惶。他(tā)的生意開始走下坡路。
這一切,阿平看在眼裏,但讓他(tā)焦慮的并不是情況變得越來越糟,而是,他(tā)發現自己面對這種情況,竟然不想做任何努力去改變點什麽,挽回點什麽。為(wèi)什麽會這樣?對此,阿平自己感到莫名(míng)其妙。
1998年,我在廈門的一個心理(lǐ)輔導中(zhōng)心接待了困擾的阿平,跟他(tā)經曆了幾次面談輔導。一年以後,我到美國(guó)修讀心理(lǐ)學(xué),這場輔導就中(zhōng)斷了。在湯普生(EarI Thompson)教授的“哀喪輔導”的課上,我回想跟阿平經曆的那個心理(lǐ)輔導過程,更加深切地意識到,阿平内心裏未經處理(lǐ)的哀喪是導緻他(tā)個人危機的深層根源。
在這裏,我讀到鮑比(John Bowlby)在他(tā)的《喪失》(Loss)中(zhōng)進行的分(fēn)析,他(tā)說,處于哀喪的人往往會“不顧一切地投身于一場社會、政治運動中(zhōng)去,試圖把自己從發生的喪失事件中(zhōng)抽離出來,好讓自己從傷痛中(zhōng)恢複過來”。但是,這樣做不能(néng)使他(tā)們内心的哀傷得到适當的表達,反而被忽略了,被擱置起來了,而這種未能(néng)表達的哀喪之情會一直潛伏于心,給當事人造成更加深切且隐而不察的損害。
阿平的情形正是如此,他(tā)内心有(yǒu)一個“沒有(yǒu)完成的哀喪”,在暗中(zhōng)從内到外影響着他(tā),使他(tā)在生活中(zhōng)的一切擺脫傷痛的努力都變得無效,甚至事與願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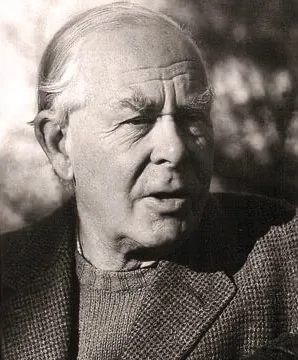
據阿平講述,女兒在自殺之前,對男朋友有(yǒu)極強的控制和獨占行為(wèi),而這可(kě)能(néng)與她早年被迫與父母分(fēn)離存在某種聯系。事後加以分(fēn)析,父母長(cháng)期離開,很(hěn)可(kě)能(néng)給她的心理(lǐ)造成不安(ān)全感和被抛棄感,由此讓她産(chǎn)生自卑的情緒,對關系缺乏信任。
我們發現,父母離開孩子,總會有(yǒu)自己的道理(lǐ),不外乎“沒有(yǒu)辦(bàn)法”、“要多(duō)掙些錢,為(wèi)了孩子過更好的生活”,等等,但是,面對父母的離開,孩子會産(chǎn)生分(fēn)離焦慮,她内心的體(tǐ)驗很(hěn)可(kě)能(néng)是:“因為(wèi)我不夠可(kě)愛,所以爸爸媽媽不要我了。”但孩子又(yòu)不敢表達出來,怕父母責怪自己不懂事,因此,她會強求自己“懂事”,為(wèi)了“懂事”而壓抑自己的需求和情感。長(cháng)期沒有(yǒu)父母的陪伴,她無法跟父母建立起适當的、滿足及安(ān)全需求的依戀關系,内心留下一種情感的空缺,而這種空缺會以極端的方式尋求補償性的滿足,用(yòng)鮑比的詞彙來說,就叫“焦慮性關系渴求”。她跟男朋友建立關系時,會表現出強烈的控制與占有(yǒu)行為(wèi),這便是受到無意識代償需求或“焦慮性關系渴求”的驅動。當男朋友試圖擺脫這種被控制、被占有(yǒu)的關系模式時,她從中(zhōng)體(tǐ)驗到的是“被抛棄”的感覺,而且,這種體(tǐ)驗又(yòu)與幼年“被父母抛棄”的體(tǐ)驗聯系起來,并且受到強化,把她投進絕望的情緒,導緻她在絕望中(zhōng)自殺。
事實上,在女兒自殺之前,阿平一度覺察到她身上那種焦慮不安(ān)的情緒,也曾想過帶她來接受心理(lǐ)咨詢,但在他(tā)忙碌的事務(wù)中(zhōng),這個念頭一閃即逝。女兒死後,阿平追悔莫及,自責不已,頭腦裏反複出現一個控制不住的想法:如果帶女兒去接受心理(lǐ)咨詢,她就不會走到自殺這一步。
在女兒活着的時候,阿平像生活中(zhōng)許多(duō)人一樣,對自己說,現在很(hěn)忙,将來有(yǒu)的是時間跟女兒在一起。在女兒離開之後,他(tā)突然意識到,這些年來,他(tā)把自己所有(yǒu)的時間都給了公(gōng)司,給女兒的時間和愛卻是那樣的少。這種無法表達的後悔和自責,在他(tā)的内心積聚着,形成了一種憤怒的情緒,一種要毀掉什麽來發洩一通的情緒。
據哀喪輔導理(lǐ)論,喪親者内心裏有(yǒu)憤怒,他(tā)們或者用(yòng)這種憤怒來懲罰自己,或者把這種憤怒傾瀉到周圍的人身上。而在潛意識裏,阿平發洩憤怒的對象是他(tā)自己和他(tā)一手經營的公(gōng)司——他(tā)恨自己太自私,恨公(gōng)司拖累了他(tā),使他(tā)沒有(yǒu)時間去關心自己的女兒,竟然導緻女兒的慘死。伴随這種憤怒和自責的情緒,阿平的潛意識裏還産(chǎn)生了一種補償女兒、給自己贖罪的願望,他(tā)采用(yòng)的方式就是對公(gōng)司不管不顧,讓公(gōng)司(連同自己的生活)成為(wèi)女兒的殉葬品。當然,阿平的這種行為(wèi)是出自他(tā)的潛意識,目的是用(yòng)來減輕内心劇烈罪疚感的折磨。他(tā)這樣做的時候,對其行為(wèi)背後的動機并不覺察,因此,他(tā)對自己的情況感到“莫名(míng)其妙”。
内疚感是從良心裏發出的“悄聲細語”,它的功用(yòng)是讓人辨别善惡是非,激勵人的德(dé)行。但是,并非所有(yǒu)的内疚感都産(chǎn)生良好的作(zuò)用(yòng),還有(yǒu)一種神經質(zhì)的内疚感,它出自過于敏感的良心,常常激發人去毀壞自己,以贖清内心被誇大的罪過。按弗洛伊德(dé)的說法,這種神經質(zhì)的内疚感會用(yòng)“悄聲細語”對潛意識說話——“我需要得病”或“我需要受苦”。
在女兒死後,阿平一度陷入激烈的沖突:一方面,他(tā)不顧一切地投身于工(gōng)作(zuò),不給自己片刻去想女兒的死;但另一方面,他(tā)越是把時間和精(jīng)力投諸生意,良心的折磨就越發劇烈。
如果用(yòng)語言來描述這種體(tǐ)驗,阿平内心的聲音是這樣的:女兒死了,阿平依然活着,公(gōng)司依然活着。他(tā)辦(bàn)公(gōng)司做生意,并沒有(yǒu)給女兒帶來他(tā)曾經想當然的那種幸福,反而剝奪了一個父親本來可(kě)以給女兒的愛。後來,阿平的公(gōng)司開始出現問題,但阿平卻聽從了他(tā)潛意識的聲音,任憑問題堆積,也不想去處理(lǐ)了。這種行為(wèi)似乎在說:女兒已經死掉了,公(gōng)司也沒有(yǒu)存在的意義了。女兒不能(néng)“從死中(zhōng)複活”,何必讓公(gōng)司“起死回生”?因此,阿平讓公(gōng)司垮掉,從現實角度來看,這是一種損失,但從潛意識層面來看,這卻可(kě)以緩解阿平内心劇烈的内疚感。所以,阿平對公(gōng)司不管不顧,其實源自心理(lǐ)防禦機制的作(zuò)用(yòng),表現為(wèi)他(tā)試圖通過一種轉移或投射的方式,讓自己遠(yuǎn)離可(kě)怕事件給他(tā)造成的心理(lǐ)沖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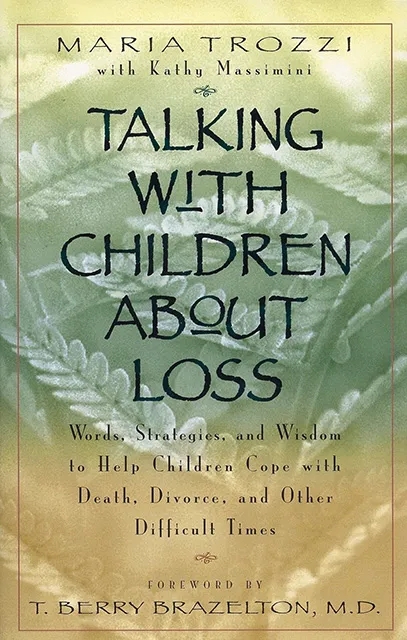
這種心理(lǐ)反應,正如特蘿翠(Maria Trozzi)在《跟孩子談喪失》(Talking with Children about Loss)中(zhōng)所說,“可(kě)能(néng)暫時使人感到安(ān)全和正常一點,但它不是真實的,它來自于一種奇幻思維”,并不能(néng)真正幫助阿平渡過危機。“切記,”特蘿翠繼續說,“要想使哀傷減輕,最好的方式不是隐藏哀傷,而是把哀傷表達出來。”
人生無常,困擾時生。當遭受不明原由的喪失事件的襲擊,人們常常發問:“為(wèi)什麽會發生在我身上?”因為(wèi)它如此痛苦,人們接下來的反應便是試圖調用(yòng)心理(lǐ)防禦機制來回避它。阿平失掉女兒之後,他(tā)沒有(yǒu)經曆哀喪的過程,反而把失親之痛壓抑下去,掩藏起來,這是造成他(tā)心理(lǐ)困擾與生活危機的深層原因。對阿平的輔導,很(hěn)重要的是協助他(tā)完成一個被擱置起來的哀喪過程。
這個過程包括:阿平可(kě)以跟妻子一同經曆哀喪,接納彼此的哀傷情緒。阿平可(kě)以跟妻子一起談論他(tā)們的女兒,而不是一味回避這個話題。阿平要能(néng)夠接受,喪失是人生難免的事情,哀喪是生命自然的情緒。阿平意識到,他(tā)是一個有(yǒu)限的人,會在生活中(zhōng)有(yǒu)所喪失;他(tā)具(jù)有(yǒu)人的情感,當遭遇喪失的時候,可(kě)以表達自己的哀喪之情。我們在生活中(zhōng)損失一件物(wù)品,都會在内心裏引起哀喪的情緒,何況我們失喪了親人。阿平知道,哀喪需要一個過程,任何一種可(kě)以被稱做哀傷的情緒,都不可(kě)能(néng)被完全抹去,也不會一下子得到醫(yī)治。
哀喪還是一個自然的過程。當一個人遭遇喪失之痛,會産(chǎn)生一個強烈的願望:忘掉它。但不管這種願望多(duō)麽強烈,總是不能(néng)忘記。或者,他(tā)以為(wèi)忘掉了,那不過是把它放到潛意識裏去了,它還在對我們說話,我們需要覺察它的存在。
榮格曾說,每一個人都扛着他(tā)自己的整個曆史,而他(tā)的生命結構裏,甚至記錄着人類的曆史,而曆史參與了我們的現在,每時每刻都在對我們說話。喪失的親人既是我們的曆史,也同時在參與我們的現在。哀喪的過程,也是一條生命領悟的路。當我們在談論喪失的親人時,我們也在了解和确認,并給現在的生活賦予新(xīn)的意義。我們感知到的每一件事情,不論好的、壞的、快樂的、悲傷的,都以某種形式聚集和貯存在我們生命内部的某個地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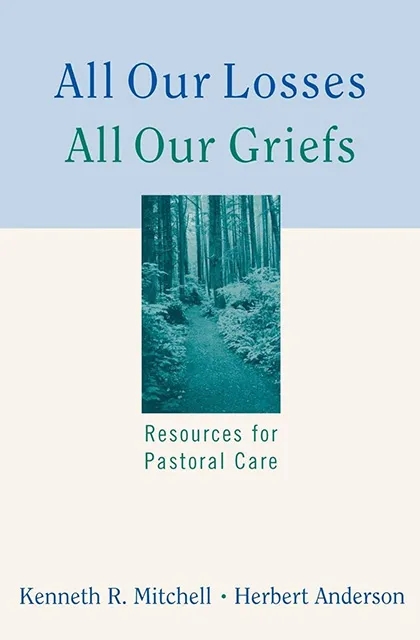
米契爾(Kenneth R. Mitchell)和安(ān)德(dé)森(Herbert Anderson)在《喪失與哀傷》(All Our Losses,All Our Griefs)中(zhōng)說:“适當表達哀傷并不是要讓我們完全忘掉喪失的對象,而是讓喪失的對象被充分(fēn)地激活,從而在生活中(zhōng)建立新(xīn)的關聯,創造新(xīn)的價值。其實,我們并沒有(yǒu)真正失掉所愛的人,他(tā)們活在我們的記憶裏,這記憶會一直豐富我們的生活,但不必要也不應該占據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空間。适當的哀喪表明我們既能(néng)帶着過去的記憶生活,又(yòu)能(néng)建立新(xīn)的關系。”
作(zuò)為(wèi)幫助人經曆哀喪的輔導者,我們需要有(yǒu)足夠的謙卑去承認,對生活中(zhōng)發生的許多(duō)事情,我們自己并不真正明白。當然,承認這一點并不意味我們什麽都不要做了,相反,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可(kě)以選擇有(yǒu)所作(zuò)為(wèi)。如特蘿翠所說:“我們并不真正懂得死亡,但我們可(kě)以用(yòng)誠實和開放的态度來分(fēn)享對它的理(lǐ)解。”
受苦是一件超越我們理(lǐ)解能(néng)力的事,但我們卻可(kě)以從受苦中(zhōng)學(xué)習,了解它對我們的意義,了解我們作(zuò)為(wèi)人的有(yǒu)限,并且學(xué)會接受。米契爾和安(ān)德(dé)森表示:“喪失以及與其相伴的哀喪都是生活不可(kě)分(fēn)割的部分(fēn),人類無法跨越受苦與死亡的界限,悲傷也是人類無法逃脫的疆域。大體(tǐ)來說,要對‘為(wèi)什麽我們要受苦?’這個人們總提的問題做出回答(dá),答(dá)案其實是簡單的:‘我們受苦,是因為(wèi)我們是人。’”
存在主義心理(lǐ)治療,對我們理(lǐ)解人生、從事哀喪輔導提供了借鑒。苦難總會臨到我們,這一點我們無法改變,但我們可(kě)以選擇對它持有(yǒu)怎樣的态度,以及做出怎樣的回應。人并不被發生的事情所注定,我們過怎樣的生活,取決于我們對發生的事持有(yǒu)怎樣的态度以及做出怎樣的反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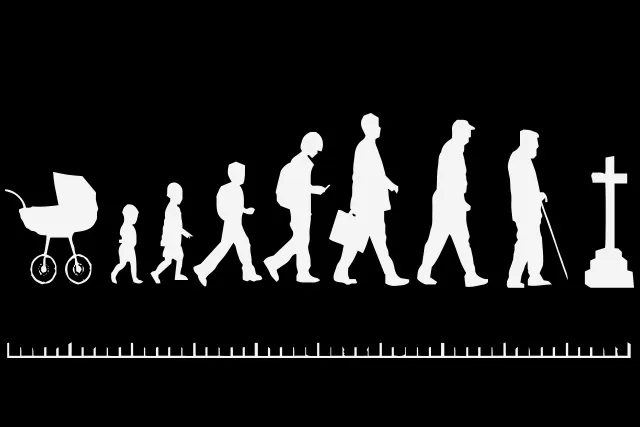
弗蘭克爾(Victor Frankl)曾在他(tā)的《追尋生命的意義》(Man’s Search for Meaning)中(zhōng)說,人類的一切生存條件都可(kě)能(néng)被剝奪,但“還有(yǒu)一樣東西保留下來了,那是人類最後的自由——在不管何種境況中(zhōng)選擇自己态度的能(néng)力”。甚至,弗蘭克爾表示,人可(kě)以在受苦中(zhōng)找到意義,從而“把一場個人悲劇轉化成一場勝利,把自我的困境轉換成人類的成就”。
因此,對于阿平來說,對于任何人來說都可(kě)以如此,一個挫折可(kě)以激發一場突破,一場危機裏同時含有(yǒu)危險與機會,我們可(kě)以做出選擇。人生充滿得與失,我們正是通過對得與失做出好的回應來創造着生活的意義。生活本身是一個意義采撷的過程,生活事件有(yǒu)“好”有(yǒu)“壞”,并非隻有(yǒu)“好”才讓人生有(yǒu)意義,“壞”裏同樣含有(yǒu)意義,甚至含有(yǒu)更深的意義,這意義需要我們進行深度采撷。
注:本文(wén)是王學(xué)富博士在2000年左右,在美國(guó)修學(xué)《哀傷輔導》課程時,所撰寫的英文(wén)論文(wén)的翻譯稿,後在2010年,文(wén)章被收錄于王學(xué)富著作(zuò)的《受傷的人》書籍裏。

直面心理(lǐ)治療系列《受傷的人》
”王學(xué)富的書“ 淘寶店(diàn)鋪有(yǒu)售

手機淘寶APP,掃描進店(diàn)
或店(diàn)鋪搜索“王學(xué)富的書”